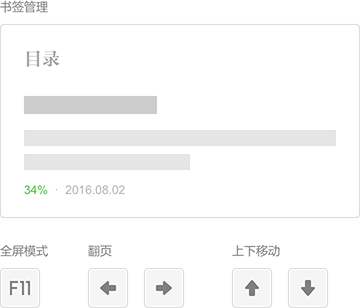第五章-我像是咖啡豆,随时有粉身的准备
第五章-我像是咖啡豆,随时有粉身的准备
我像是咖啡豆,随时有粉身的准备
亲爱的你,请将我磨碎
我满溢的泪,会蒸馏出滚烫的水
再将我的思念溶解,化为少许糖味
盛装一杯咖啡
陪你度过,每个不眠的夜
台中到了,这是荃的家乡。
荃现在会在台中吗?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右肩又感到一阵抽痛。
因为我想到了荃。
我的右肩自从受伤后,一直没有完全复原。
只要写字久了,或是提太重的东西,都会隐隐作痛。
还有,如果想到了荃,就会觉得对不起明菁抽搐的背。
于是右肩也会跟着疼痛。
看到第七根烟上写的咖啡,让我突然很想喝杯热咖啡。
可是现在是在火车上啊,到哪找热咖啡呢?
而只要开水一冲就可饮用的三合一速泡咖啡,对我来说,跟普通的饮料并无差别。
我是在喝咖啡喝得最凶的时候,认识荃。
大约是在研二下学期,赶毕业论文最忙碌的那阵子。
那时一进到研究室,第一件事便是磨咖啡豆、加水、煮咖啡。
每天起码得煮两杯咖啡,没有一天例外。
没有喝咖啡的日子,就像穿皮鞋没穿袜子,怪怪的。
这种喝咖啡的习惯,持续了三年。
直到去年七月来到台北工作时,才算完全戒掉。
今年初看到痞子蔡写的《爱尔兰咖啡》,又勾起我喝咖啡的欲望。
写封E-mail问他,他回信说他是在台南喝到爱尔兰咖啡,
而非在小说中所描述的台北。
他也强调,只要是道地的爱尔兰咖啡,在哪喝都是一样的。
爱尔兰咖啡既然崇尚自由,自然不会限制该在哪种咖啡馆品尝。
他在信尾附加了一段话,他说爱尔兰咖啡对他而言,是有意义的。
但对别人来说,可能就只是一种咖啡而已,没什么了不起。
与其想喝属于别人的爱尔兰咖啡,不如寻找属于自己的珍珠奶茶,或是可口可乐也行。
就像是明菁送我的那株檞寄生一样,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但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根金黄色的枯枝而已。
明菁说得没错,离开寄主的檞寄生,枯掉的树枝会逐渐变成金黄色。
我想,那时刚到台北的我,大概就是一根枯掉的檞寄生枝吧。
别人找的是饮料,我找的,却是新的寄主植物。
可是对于已经枯掉的檞寄生而言,即使再找到新的寄主,也是没意义的。
从台北到台中,我已经坐了二个小时又四十五分钟的火车。
应该不能说是"坐",因为我一直是站着或蹲着。
很累。
只是我不知道这种累,是因为坐车?
还是因为回忆?
这种累让我联想到我当研究生时的日子。
考上研究所后,过日子的习惯开始改变。
我、柏森、子尧兄和秀枝学姐仍然住在原处,孙樱和明菁则搬离胜九舍。
孙樱在工作地方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套房。
明菁搬到胜六舍,那是研究生宿舍,没有门禁时间。
孙樱已经离开学生生活,跟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少。
少得像八十岁老人的牙齿。
不过这少许的连系就像孙樱写的短篇小说一样,虽然简短,但是有力。
这力量几乎摇撼我整个人生。
我会认识荃,是因为孙樱。
其实孙樱是个很好的女孩子,有时虽然严肃了点,却很正直。
我曾以为柏森和孙樱之间,会发生什么的。
"我和孙樱,像是严厉的母亲与顽皮的小孩,不适合啦。"柏森说。
"可是我觉得孙樱不错啊。"
"她是不错,可惜头不够圆。"
"你说什么?"
"我要找投缘的人啊,她不够头圆,自然不投缘。"柏森哈哈大笑。
我觉得很好奇,柏森从大学时代,一直很受女孩子欢迎。
可是却从没交过女朋友。
柏森是那种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哪种女孩子的人。
如果他碰上喜欢的女孩子,一定毫不迟疑。
只不过这个如果,一直没发生。
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喜欢哪种女孩子。
就像吃东西一样,我总是无法形容我喜欢吃的菜的样子或口味等等。
我只能等菜端上来,吃了一口,才知道对我而言是太淡?还是太咸。
认识明菁前,柏森常会帮我介绍女孩子,而且都是铁板之类的女孩。
其实他也不是刻意介绍,只是有机会时就顺便拉我过去。
"柏森,饶了我吧。这些女孩子我惹不起。"
"看看嘛,搞不好你会喜欢喔。"
"喜欢也没用。老虎咬不到的,狗也咬不到啊。"
"你在说什么?"
"你是老虎啊,你都没办法搞定了,找我更是没用。"
"菜虫!你怎么可以把自己比喻成狗呢?"
柏森先斥责我一声,然后哈哈大笑:
"不过你这个比喻还算贴切。"
认识明菁后,柏森就不再帮我介绍女孩子了。
"你既然已经找到凤凰,就不用再去猎山鸡了。"柏森是这样说的。
"是吗?"
"嗯。她是一个无论你在什么时候认识她,都会嫌晚的那种女孩子。"
会嫌晚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对那时的我而言,明菁的存在,是重要的。
没有明菁的话,我会很寂寞?还是会很不习惯?
我不敢想象,也没有机会去想象。
如果,我先认识荃,再认识明菁的话,我也会对荃有这种感觉吗?
也许是不一样的。
但人生不像在念研究所时做的实验,可以反复地改变实验条件,
然后得出不同的实验结果。
我只有一次人生,无论我满不满意,顺序就是这样的,无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