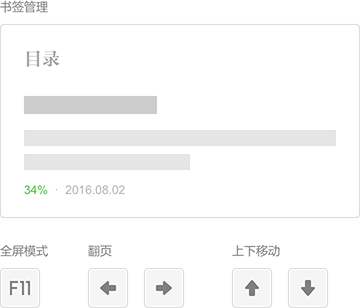序言
序言
大家好,很久不见,甚念。
《简单爱》比预想的多写了两个月,我一直在怀疑,到底有没有表达出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之前我另写了一部小说,不大满意,合同都签了还是压下了没有出版,《简单爱》写得比较匆忙。感谢责编尹老师,人忒好,一次又一次纵容我的拖稿,告诉我“质量第一”。
《简单爱》是我写的第一部非悲剧结尾的小说,其实写惯悲剧,总恨不得搞成飞鸟各投林式的结尾,留一片白茫茫大地去勾引读者眼泪,这次本来也习惯性的往悲剧那边偏,朋友不让,给我发《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言财色之于人,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说我本来就是对于生活中阴暗部分分外敏感的人,长久执著于此,心里全是灰暗,正如刀头舔蜜,所得甚少,所失甚多。
她说,你每次写完什么,看起来就像病了一场。
被朋友劝下了,心下不甘,下回吧,理想中的下一部作品应该是集变态狗血悲剧之大成的变态文本。毛主席讲了,“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
但是不写悲剧怎么办呢?我们的世界是多么像一个笑话。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些看起来阳光灿烂,笑话不断,玩世不恭的家伙们,内心多半是灰白无力的。憨豆先生给全世界送去了笑声,但他本人是抑郁症患者,而这几乎是喜剧界的通病,无论是金-凯瑞还是萨多-帕尔拉,都难逃人前欢笑人后抑郁的下场。据说周星驰在生活中是个阴沉严肃的人,其实他的作品也未必就全是搞笑,《喜剧之王》扔掉假惺惺的结尾,完全是一部严肃的悲剧。病态的沉积很容易走向反面,古汉语中有一个词专门形容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叫做“痛咥”。我们都觉得美国文化肤浅而轻松,大导演伍迪-爱伦却一针见血地撕下了鬼脸上的美丽画皮:“你这样地悲观绝望,这样地看破一切,你惟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
每当听到“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快乐起来”这种言论的时候,都会条件反射地想起《东成西就》中周伯通的名言,“师弟,你为何要强颜欢笑呢?”
黄药师抱头痛哭,“师兄,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我不是聪明女生》和《别走,我爱你》都有读者表示写得太残酷,请原谅,我只能那样写,角色性格一旦设定,慢慢就都有了生命,他们自己走完剩下的剧本,与我无关。你我都知道蛇不会去吃树的,啮树不过是为了发泄体内盛极而爆的剧毒。对蛇来说,这棵树与另外的树并无不同,只是作为一个见证并承担痛苦的标记而存在着罢了。我那样写,因为我只能那样写,别无选择。
《简》大体上可算我正式变态前的一个练手,这是最后的余温,回光返照的一瞬,为什么这么怀恋少年时的温情,因为它最单纯可贵。如果我们能够有怜悯。我们该如何地沉默,如何拥抱。谁又能够来告诉我们,如何来穿越这漫长的绝望?
我始终是个对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心生畏惧的人,是个懦弱无用的人。
写小说的同时还开始写了一系列关于三国水浒的短章,读中学的时候最喜欢《与妻书》和前、后《出师表》,觉得很感人。我私心里是比较希望写这样的东西的,一样世情百态,但是事不关己,所以写起来心里不累。希望有机会能拿给大家看,感谢你们对我一如既往的理解和支持,你们的理解让我感到温暖,亦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董晓磊
2007年11月28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