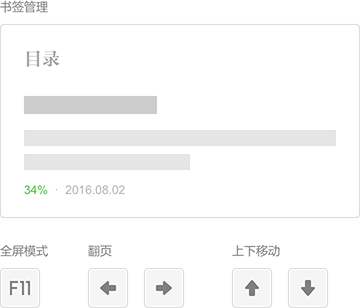第二卷 险情丛生(1)
第二卷 险情丛生(1)
一险情丛生
一月,夜幕很早就降临了。格兰古瓦从司法宫出来,街上已是一片昏暗。这降临的夜幕,倒使他感到高兴;他巴不得即刻钻进哪条阴暗寂寥的小巷,好无拘无束地进行思考,让他这哲人先包扎一下他这诗人的创伤。况且,他不知何处安身,只有哲理是他唯一的栖身之所。初次涉足戏剧就惨遭夭折,他不敢回到草料港对面的水上谷仓的寓所去;本来指望府尹大人会给他的祝婚诗一点赏钱,好还清巴黎屠宰税承包人吉约姆·杜克斯—西尔六个月的房租,一共十二巴黎索尔,相当于他所有东西价值的十二倍,包括他的短裤、衬衫和铁面盔都估计在内。他暂时躲在圣小教堂司库那间监牢般房子的小门洞里,盘算片刻,既然巴黎所有马路随他挑,得选一个过夜的窝。他想起上星期曾在旧鞋铺街发现吏部某咨议的家门口有块供骑驴用的脚踏石,并曾暗自想过,这块石头需要时倒可以给乞丐或诗人充当枕头,那是再妙不过了。感谢上苍赐给他这样一个好主意!他便准备动身穿越司法宫广场到老城去,那里一条条宛如姐妹的古老街道,诸如桶坊街,老呢布坊街,旧鞋铺街,犹太街等等,七拐八弯,纵横交错,真是曲曲折折的一座迷宫,至今那些十层楼房还屹立在那里哩。
然而正在这时候,他突然看见狂人教皇的游行队伍也从司法宫出来,大喊大叫,火把通明,还由他——格兰古瓦——的乐队奏着乐曲,浩浩荡荡蜂拥而来,挡住他的去路。这一见呀,他自尊心所受的创伤又剧痛起来,遂拔腿躲开了。他惨遭不幸的遭遇,苦不堪言,凡是能使他回想起这天有关节日的一切,都感到痛苦难当,伤口在淌血。
他打定主意,取道圣米歇尔桥,不料那儿有成群的孩子拿着花筒和冲天炮到处奔跑。
“该死的烟花炮仗!”格兰古瓦说道,赶忙折回,奔到兑换所桥。桥头的一些房屋上悬挂三面旗帜,分别画着王上、王太子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的肖像,还有六面小旌旗,上面的画像分别是奥地利大公、波旁红衣主教、博博热殿下、法兰西雅娜公主、波旁的私生子亲王,以及另一位什么人。这一切被火把照得通亮。群众赞赏不已。
“约翰·富尔博画家真走运!”格兰古瓦长叹一声,说道。
话音一落,随即转过身去,不再看那些大小旗子了。面前有一条街道,黝黑黑的,冷落落的,正好是避开节日一切回响和一切辉映的好去处。他一头钻了进去,过了片刻,脚被什么东西一绊,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原来是五月树花束。
司法宫的书记们为了庆祝这隆重的节日,清早把它拿来放在吏部尚书的家门口。这新的遭遇,格兰古瓦二话没说,忍住了,随后爬起来,走到塞纳河边去。民事法庭小塔楼和刑事法庭的大塔楼全被抛在身后,沿着御花园的大墙往前走,踩着那没铺路石、烂泥齐踝深的河滩,来到老城的西端,眺望了牛渡小洲一会儿。这个小洲今天已不见了,就在那座铜马和新桥下面。当时,他觉得小洲像一堆乌黑的东西出现在微白色狭窄水面的那一边,借着一盏小灯的光线,隐约可见到一间蜂房似的草屋,想必那是给牛摆渡的艄公宿夜之处。
“走运的摆渡艄公呀!”格兰古瓦思忖着。“你不企盼荣华,不必写庆婚诗!什么王室结婚啦,什么勃艮第女大公啦,统统与你无干!你除了知道四月的草场上雏菊盛开,供你的母牛作饲料外,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什么雏菊!而我身为诗人,却受到喝倒彩,冻得直打哆嗦,负债十二个索尔,而且鞋底磨得透明,可以给你做灯罩玻璃。谢谢!摆牛渡的船夫!你那小茅屋擦亮了我眼睛,教我把巴黎丢诸脑后!”
霍然间,从极乐小屋那边传来圣约翰教堂巨大双响炮仗的响声,把他从近乎诗情画意的消魂荡魄中惊醒过来。原来是摆渡的艄公也在这节日里乐一乐,放了一个烟花炮仗。
这炮仗把格兰古瓦炸得毛骨悚然。
“该死的节日!”他叫了起来。“你到处对我紧追不舍吗?啊!我的上帝呀!你一直追到这船夫的小屋里!”
话一说完,瞧了一眼脚下的塞纳河,突然产生一个可怕的念头:
“噢!要是河水不这么冰凉,我宁愿投河自尽,一死了之!”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既然无法摆脱狂人教皇,无法摆脱约翰·富尔博的旌旗、五月树的花束、炮仗和爆竹,那倒不如放大胆子投入节日的狂欢中去,到河滩广场去!
“到河滩广场去,起码有焰火的余焰可以暖一暖身子;为全市公众提供的冷餐,想必已架起摆满国王甜点心的三大食品柜,至少可以去检点面包残屑,聊当晚餐。”
二河滩广场
昔日的河滩广场,如今已依稀难辨了。今日所见到的只是广场北角那座雅致的小钟楼;就是这小钟楼,几经胡乱粉刷,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其雕刻的生动棱线变得臃肿粗糙,兴许很快就像巴黎所有古老建筑的正面,迅速被那涨潮般的新房屋所吞噬那样,也将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这座被夹在路易十五时代两幢破房子中间的小钟楼,任何人经过河滩广场,都会像我们一样,不会不向它投过去同情和怜悯的目光;谁都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它当初所属全部建筑物的原貌,并可以从中再现十五世纪这峨特式古老广场的全景。
那时的广场就像今天的一样,呈不规则的梯形,一边是塞纳河岸,另三边是一连串狭窄而阴暗的高大屋宇。白天,可以观赏广场周围多种多样风格的建筑物,全是用石块或木头雕刻而成,中世纪各种住宅建筑风格的式样应有尽有,从十五世纪可上溯到十一世纪,从开始取代尖拱窗户的格子窗户,直到尖拱窗户取代罗曼式圆拱窗户,样样齐备;这种罗曼式圆拱窗户,在广场凭临塞纳河的一角,紧靠鞣革作坊的那一边,罗朗塔楼那座古老房屋的二楼,在尖拱窗户的下边,仍保留着这种风格。夜里,这一大堆建筑物,只见屋顶锯齿状的黑影,好似一条由许多锐角组成的链条环绕着广场。因为往昔都市与现今都市最根本的差异之一,就在于今天的都市都是房屋的门面朝向广场和街道,而以往却是房屋的山墙。两个世纪来,房屋的坐向恰好掉转了个方向。
广场东边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建筑物,笨重而混杂,由三个宅所重叠组成。这座庞然大物有三个名称,可以说明其沿革、用途和建筑风格;储君院,因为查理五世为王储时曾在此居住;商业厅,因为它曾经作为市政厅;柱子阁(domusadpiloria),由于整座四层楼由一系列粗大的柱子支撑着。像巴黎这样一个美好都市所需的一切,这里应有俱有:有一座小教堂,可供祈祷上帝;一大间辩护堂,可供接见、或者必要时顶撞国王派来的人;而且在阁楼上有一间装满枪炮的兵器库。这是因为巴黎的市民都晓得,在任何情况下,光凭祈祷和上诉是不足以保障巴黎市民权的,所以在市政厅的阁楼上才一直储存着生了锈的某种精良的弩炮。
打从那时起,河滩便是这种凄凉的景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令人产生一种厌恶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多米尼克·博卡多建造的阴森森的市政厅代替了柱子阁。应当说明一下,铺着石板的广场正中央,长年累月并肩竖立着一座绞刑台和一座耻辱柱——当时人们称做“正义台”和“梯子”,也起了不小的坏作用,叫人惨不忍睹,迫使人们把视线从这可怖的广场移开。在这里曾有多少生龙活虎般的健儿断送了生命!也是在这里,五十年后发生了所谓圣瓦利埃热病①那种断头台恐怖症:这是所有病症中最叫人毛骨悚然,因为它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顺便说一句,三百年前死刑在这里肆虐,到处仍是铁碾②,石条绞刑台,深陷在石路面上常年搁置在那里的形形色色刑具,这一切堵塞了河滩、菜市场、储君广场、特拉瓦十字教堂、猪市场、阴森可怖的鹰山、捕头哨卡、猫广场、圣德尼门、尚波、博代门、圣雅各门、尚且不算那些府尹、主教、教士会教士、住持、修道院院长在这里伏法的数也数不清的“梯子”;尚且也不算塞纳河中的溺刑场;所有这一切如今已不复存在,每想到此,多少感到宽慰。今天,死神的片片盔甲已坠落,其排场阔绰的酷刑、异想天开的刑罚、每五年在大堡重换一张皮革床③的严刑拷打,统统已相继被废除了;死神这封建社会的老霸王,几乎被逐出我们的法律,被逐出我们的都市,一部又一部法典加以追究,一个广场又一个广场加以驱赶,如今在我们广大的巴黎,只剩下河滩广场上一个可耻的角落还有一座可怜巴巴的断头台,鬼鬼祟祟,慌恐不安,丢人现眼,仿佛老是提心吊胆,生怕干坏事被人当场逮住——因为它每次干完勾当就马上溜之大吉,所有这一切叫人怎能不感到欣慰呢!
①圣瓦利埃为查理八世的将领。查理八世为了取得对那不勒斯的继承权,对意大利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惨败而归,导致大批法国人死亡。这种“热病”就是指这场灾难。
②指碾刑。这是中世纪一种酷刑,先把犯人砍去四肢,再用铁碾把犯人身子碾成肉泥。
③也是一种酷刑,把犯人绑在皮革制的床架上,进行残酷的鞭笞。
三“以吻换揍”
(BesosParaGolpes)
皮埃尔·格兰古瓦来到河滩广场,全身都冻麻木了。为了免得碰上兑换所桥上嘈杂的人群,免得再瞅见约翰·富尔博所画的旌旗,他故意取道磨坊桥;可是主教所有那些水磨轮子都在旋转,他走过时,还是溅了一身水,连粗布褂儿都湿透了。而且他觉得,由于剧本演出惨遭失败,益发怕冷了。
于是,急忙向广场中央燃烧得正旺的焰火走近去。然而,焰火四周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
“该死的巴黎佬!”他自言自语,因为格兰古瓦身为真正的戏剧诗人,独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们竟把火给我挡住了!
可我迫切需要站在哪个壁炉角落里烤一烤火。我脚上的鞋子喝足了水,那些该死水磨哭哭泣泣,浇了我一身!巴黎主教开磨坊真是鬼迷心窍!我倒真想知道一个主教要磨坊有什么用!难道他期待从主教变成磨坊老板吗?如果他为此只欠我的诅咒的话,我马上就给他,给他的大教堂和磨坊!请瞧一瞧这班游手好闲的家伙,他们是不是挪动一下位置!我倒要请教一下,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他们在烤火取暖,妙哉!在望着千百捆柴禾熊熊燃烧,多么壮观呀!”
走前仔细一看,才发现群众围成的圆圈比取暖所需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观众并不单纯是受千百捆柴禾燃烧的美景所吸引才蜂拥而来的。
原来是在人群与焰火之间一个宽阔的空地上,有个少女在跳舞。
这位少女究竟是人,还是仙女,或是天使,格兰古瓦尽管是怀疑派的哲人,是讽刺派的诗人,一上来也拿不准,因为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使他心醉神迷了。
她身材不高,可苗条的身段挺拔,显得修长,所以他仿佛觉得她个儿很高。她肤色棕褐,但可以猜想到,白天里看上去,大概像安达卢西亚姑娘和罗马姑娘那样有着美丽的金色光泽。她那纤秀的小脚,也是安达卢西亚人的样子,穿在优雅的鞋子里整个显得贴紧而又自如。她在一张随便垫在她脚下的旧波斯地毯上翩翩舞着,旋转着,涡旋着;每次一旋转,她那张容光焕发的脸蛋儿从您面前闪过,那双乌亮的大眼睛就向您投过来闪电般的目光。
她周围的人个个目光定定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果然不假,她就这样飞舞着,两只滚圆净洁的手臂高举过头上,把一只巴斯克手鼓敲得嗡嗡作响;只见她的头部纤细,柔弱,转动起来如胡蜂似那样敏捷;身著金色胸衣,平整无褶,袍子色彩斑烂,蓬松鼓胀;双肩裸露,裙子不时掀开,露出一对优美的细腿;秀发乌黑,目光似焰;总之,这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尤物。
“真的,这是一个精灵①,一个山林仙女,一个女神,梅纳路斯山的一个酒神女祭司②。”格兰古瓦心里想着。
恰好这时,“精灵”的一根发辫散开了,插在发辫上的一支黄铜簪子滚落地上。
“哎!不对!这是个吉卜赛女郎。”格兰古瓦脱口而出,说道。
任何幻觉一下子消失了。
她重新跳起舞来。从地上拿起两把剑,把剑端顶在额头上,随即把剑朝一个方向转动,而她的身子则朝逆方向转动。
一点不假,她确确实实是个吉卜赛女郎。话说回来,尽管格兰古瓦幻觉已经消失了,但这整个如画的景观依然不失其迷人的魅力。焰火照耀着她,那红艳艳的强烈光芒,灿烂辉煌,在围观群众的脸盘上闪烁,在吉卜赛女郎褐色的脑门上闪烁,并且向广场深处投射过去微白的反光,只见柱子阁裂纹密布、黝黑的古老门面上和绞刑架两边的石臂上人影摇曳不定。
在千万张被火光照得通红的脸孔中间,有一张似乎比其他所有的脸孔更加专神贯注地凝望着这位舞女。这是一张男子的面孔,严峻,冷静,阴郁。这个男子穿着什么衣服,因为被他周围的群众挡住看不出来,年龄至多不超过三十五岁;但已经秃顶了,只有两鬓还有几撮稀疏和已经灰白的头发;额门宽阔又高轩,开始刻划着一道道皱纹;然而,那双深凹的眼睛里却迸发出非凡的青春火花,炽热的活力,深沉的欲情。
他把这一切情感不停地倾注在吉卜赛女郎身上;当他看到这个年方二八、如痴似狂的少女飞舞着,旋转着,把众人看得消魂荡魄时,他那种想入非非的神情看起来益发显得阴沉了。
他的嘴唇不时掠过一丝微笑,同时发出一声叹息,只是微笑比叹息还痛苦十分。
少女跳得气喘吁吁,终于停了下来,民众满怀爱意,热烈鼓掌。
“佳丽!”吉卜赛女郎喊了一声。
这当儿,格兰古瓦看见跑过来一只漂亮的小山羊,雪白,敏捷,机灵,油光闪亮,角染成金色,脚也染成金色,脖子上还戴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格兰古瓦原先并没有发现这只小山羊,因为它一直趴在地毯的一个角落里,望着主人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