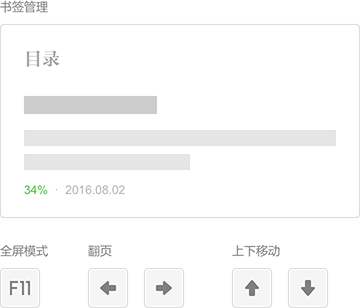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从此之后,莫可基便变成了莫可文了。从此之后,我也只说莫可文,不再说莫可基了。莫可文到了苏州,照例禀到缴凭,自不必说。他又求上头分到镇江府当差,上头自然无有不准的。他领到札子,又忙到镇江去禀到。你道他这个是甚么意思?原来镇江府王太尊是他同乡,并且太尊的公子号叫伯丹,小时候曾经从他读过两三年书的,他向来虽未见过王太尊,却有个宾东之分在那里。所以莫可文到得镇江,禀见过本府下来,就拿帖子去拜少爷,片子后面,注明‘原名可基’。王伯丹见是先生来了,倒也知道敬重,亲自迎了出来,先行下拜。行礼已毕,便让可文上坐。可文也十分客气,口口声声只称少爷,只得分宾坐了。说来说去,无非说些套话。在可文的意思,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嘘,给个差使。但是初见面,又不便直说,只说得一句‘此次到这边来,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伯丹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只当他是客气话,也支些客气话回答他。
可文住在客栈里十多天,不见动静,又去拜过两次伯丹。伯丹请他吃过一回馆子,却是个早局,又叫了四五个局来,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伯丹却倾倒的了不得。可文很以为奇,暗暗的打听,才知道王太尊自从断弦之后,并未续娶,又没有个姨太太,衙门里头,并无内眷。管儿子极严,平常不准出衙门一步,闲话也不敢多说一句。伯丹要出来顽顽,无非是推说那里文会,那里诗会,出来顽顽个半天,不到太阳下山,就急急的回去了。就是今天的请客,也是禀过命,说出去会文,才得出来的。所以虽是牛鬼蛇神的妓女,他见了就如海上神山一般,可望不可即的了。可文得了这个消息,知道伯丹还纯乎是个孩子家,虽托了他也是没用。据如此说,太尊还不知我和他是宾东呢。要想当面说,自己又初入仕途,不知这话说得说不得。踌躇了两天,忽然想了一个办法,便请了几天假,赶回杭州去。
此时,他住的两间祖屋,早已租了给人家住了。这一次回来,便把行李搬到弟妇家去。告诉弟妇:‘已经禀过到了,此刻分在镇江,不日就可以有差使了。我此刻回来,接你到镇江同住。从此就一心一意在镇江当差候补,免得我身子在那边,心在这边,又不晓得你几时没了钱用,又恐怕不能按着时候给你。因此想把你接了去,同住在一起,我赚了钱,便交给你替我当家。有是有的过法,没有是没有的过法,自己一家人,那是总好说话的。’弟妇听了他这个话,自然是感激他,便问几时动身。可文道:‘我来时只请了十五天的假,自然越赶快越好。今天不算数,我们明天收拾起来罢。’弟妇答应了。因为他远道回来,便打了二斤三白酒,请他吃晚饭。居乡的人不甚讲究规矩,便同桌吃起饭来。可文自吃酒,让弟妇先吃饭。
“等弟妇饭吃完了,他的酒还只吃了一半。却仗着点酒意,便和弟妇取笑起来,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他弟妇本是个乡下人,虽然长得相貌极好,却是不大懂得道理,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虽然知道涨红了脸,却不解得回避开去。可文见他如此,便索性道:‘弟妇,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今年才二十岁——’弟妇道:‘只有十九岁,你兄弟才二十岁呢。’可文道:‘那更不对了!你十九岁便做了寡妇,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虽说是吃的穿的有我大伯子当头,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啊。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伯子带着一个小婶,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弟妇道:‘怎样的法子呢?’可文道:‘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
弟妇听了这句话,不觉登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道:‘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不过象你那个守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街邻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证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节,岂不是白过了的么?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得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亦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咧、上馆子咧,只要我差使好,化得起,尽你去化,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么?’他弟妇始终不曾答得一句话,还伏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几日之间,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式,便搬了进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为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用了一个老妈子;又化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弟妇此时便升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假,又去拜少爷。
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诚去请王伯丹来吃饭。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向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舍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道:‘先生赏饭,自当奉陪;争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因此不便。’可文道:‘那么就改作午饭罢,务乞赏光!’伯丹只得答应了。不知又向老子捣个甚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道:‘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使,所以租不出好地方,这房子小,简慢得很。好在我们同砚,彼此不必客气,回来请到里面去坐,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伯丹连称:‘好说,好说。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坐了一会,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到得里面,伯丹便先请见师母。可文揭开门帘,到房里一会,便带了太太出来。伯丹连忙跪下叩头,太太也忙说:‘不敢当,还礼,还礼。’一面说,一面还过礼。可文便让坐,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先开口说道:‘少爷,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没有事时候,不嫌简慢,不妨常请过来坐坐。’伯丹道:‘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闲话片时,老妈子端上酒菜来,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一面是可文敬酒,伯丹谦让入座。又说‘师母也请喝杯酒’。可文也道:‘少爷不是外人,你也来陪着吃罢。’太太也就不客气,坐了过来,敬菜敬酒,有说有笑。畅饮了一回,方才吃饭。饭后,就在上房散坐。可文方才问道:‘兄弟到了这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砚的话?’伯丹道:‘这个倒不曾。’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其时有几个客籍的文人,在镇江开了个文会,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与一班文人结交。所以他在外头识了朋友,回去绝不敢提起;这回他先生来了,也绝不敢提起。在可文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自己虽不便面陈,幸得学生是随任的,可以借他说上去,所以禀到之后,就去拜少爷。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今天请他吃饭,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当下又说道:‘少爷何妨提一提呢?’伯丹道:‘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文道:‘这个又当别论。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尊大人是个官身,不便在外面体察的原故。象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务请提一提。’伯丹答应了,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太尊道:‘原来是先生,你为甚不早点说。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使呢。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伯丹道:‘十二三四岁那几年。’太尊道:‘你几岁上完篇的?’伯丹道:‘十三岁上。’太尊道:‘那么你还是他手上完的篇。’随手又检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道:‘他何尝在庠,是个监生报捐的功名。’伯丹道:‘孩儿记得清清楚楚,先生是个秀才。’太尊道:‘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家乡的事,全都糊里糊涂的了。你既然在他手下完篇的,明天把你文会上作的文章誉一两篇去,请他改改看,可不必说是我叫的。’伯丹答应了,回到书房,誉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可文读了一遍,摇头摆尾的,不住赞好道:‘少爷的文章进境,真是了不得!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只有五体投地的了!’伯丹道:‘先生不要客气,这是家君叫请先生改的。’可文兀的一惊道:‘少爷昨天回去,可是提起来了?’伯丹道:‘是的。’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一直钉住问,如何提起,如何对答,尊大人的颜色如何。伯丹不会撒谎,只得一一实说。可文听到秀才、监生一说,不觉呆了一呆,低头默默寻思,如果问起来,如何对答,须要预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揽词讼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会儿的功夫,早想定了。并且也料到叫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爷客气,拿起笔来,飕飕飕的一阵改好了,加了眉批、总批,双手递与伯丹道:‘放恣放恣!尊大人跟前,务求吹嘘吹嘘!’伯丹连连答应。坐了一会,便去了。
到了明日是十五,一班佐杂太爷,站过香班,上过道台衙门,又上本府衙门。太爷们见太尊,向来是班见,没有坐位的。这一天,号房拿了一大叠手版上去。一会儿下来,把手版往桌上一丢,却早怞出一个来道:‘单请莫可文莫太爷。’众佐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运气自然与众不同,无怪他独荷垂青了。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对众同寅拱拱手,说声‘失陪’,便跟了手版进去。走到花厅,见了太尊,可文自然常礼请安。太尊居然回安拉炕,可文那里敢坐,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开口道:‘小儿久被化雨,费心得很。老夫子到这边来,又不提起,一向失敬;还是昨天小儿说起,方才知道。’可文听了这番话,又居然称他老夫子,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怎样才好,答应也答应不出来,末末了只应得两个‘是’字。太尊又道:‘听小儿说,老夫子在庠?’可文道:‘卑职侥幸补过廪,此次为贫而仕,是不得已之举,所以没有用廪名报捐。到了乡试年分,还打算请假下场。’太尊点头道:‘足见志气远大!’说罢,举茶送客。可文辞了出来。只见一班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东站两个,西站三个的,在那里谈天。见了可文,便都一哄上前围住,问见了太尊说些甚么,想来一定得意的。可文洋洋得意的说道:‘无意可得。至于太尊传见,不过谈谈家乡旧事,并没有甚么意思。’内中一个便道:‘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可文道:‘没有,没有,不过同乡罢了。’说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换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给小家人。他的公馆近在咫尺,也不换衣服,就这么走回去了。
“从此之后,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每去,必在上房谈天,那师母也绝不回避,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点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文不在家,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的了。
“可文又打听得本府的一个帐房师爷,姓危号叫瑚斋的,是太尊心腹,言听计从的,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又请瑚斋来家里吃饭,也和请伯丹一般,出妻见子的,绝无回避。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得风蚤,逢人都有说有笑,因此危瑚斋也常常往来。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可文才求瑚斋向太尊说项。太太从旁也插嘴道:‘正是。总要求危老爷想法子,替他弄个差使当当才好。照这样子空下去,是要不得了的!这里镇江的开销,样样比我们杭州贵,要是闹到不得了,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说罢,嫣然一笑。危瑚斋受了他夫妻嘱托,便向太尊处代他说项。太尊道:‘这个人啊,我久已在心的了。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还要打听打听,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课卷,我节下送他点节敬罢了。’瑚斋道:‘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没甚么。’太尊道:‘你不知道:我看读书人当中,要就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上去的,十人之中,还有五六是个好人;若是但进了个学,补了个廪,以后便蹲蹬住的,那里头,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势。单靠着坐馆,能混得了几个钱,自然不够他用;不够用起来,自然要设法去弄钱。你想他们有甚弄钱之法?无非是包揽词讼,干预公事,鱼肉乡里,倾轧善类,布散谣言,混淆是非,甚至窝娼庇赌,暗通匪类,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他们无做不到。我府底下虽然没有甚么重要差使,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拣个好人,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说话。莫某人他是个廪生,他捐功名,又不从廪贡上报捐,另外弄个监生,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甚么事,是个被革的廪生,那就好人有限了。’瑚斋道:‘依晚生看去,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不过头巾气太重,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晚生看他世情都还不甚了了,太尊所说种种,他未必去做。’太尊道:‘既然你保举他,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既而又说道:‘他既是世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当得差呢。我看他笔墨还好,我这里的书启张某人,他屡次接到家信,说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没放他走,不如就请了莫某人罢。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瑚斋道:‘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如此一来,他虽是个坏人,也要感激的学好了。’说罢,辞了出来,挥个条子,叫人送给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见了信,直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
正是:任尔端严衡品行,奈渠机智善欺蒙。不知莫可文当了镇江府书启之后,尚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